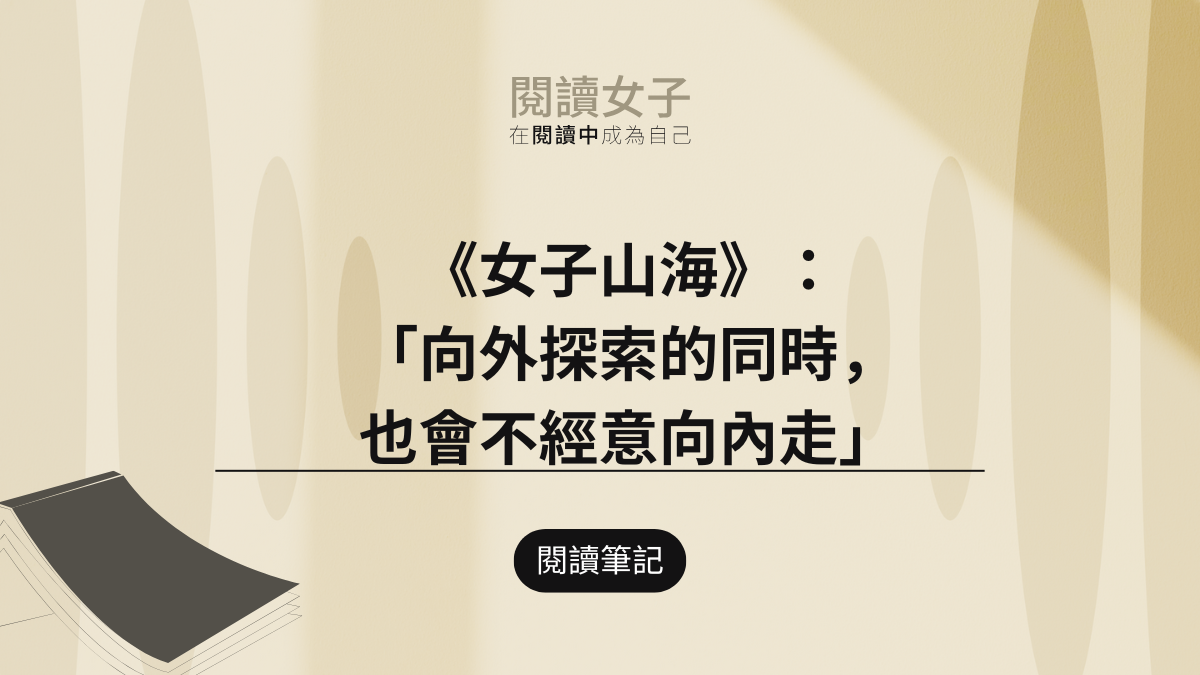一、兩名女子關於山海的對話
劉崇鳳和張卉君是大學同學兼室友,年輕時就常一起出遊,對山海與女性身份的經年探索,從厚厚一疊的往返通信,幾經修訂後匯集成書。
年輕時的壯遊,化作生命的養份。
劉崇鳳這麼寫:「多麽慶幸我們回不去了,多麽慶幸就算人事已非,我還記得這片土地所擁有的美好與哀傷,平靜與衝突。就因時間永遠昂首向前,我們才不再是浪漫的大學生,不再有長假可以御風而行,我們必須學習靠自己的力量生存,尋找一個合適的角色,參與並擾動這個社會,生命才有力量。」
兩人或是下田種米、或是擔任黑潮基金會執行長、或是帶領年輕一輩認識山林,用各種方式來「參與並擾動這個社會」。
二、在山裡直面自己的恐懼和渴望
劉崇鳳帶領一群孩子上山探索,有女孩想嘗試跳水,讓劉崇鳳紅了眼眶,我也眼睛發熱。
「我看著女孩盯著水面的眼睛,惶恐、逃避、懷疑、自我否定……什麼都有,唯一撐著她還站在那裡的,依然是渴望。我懂得、我們都懂得,山也會迫使我們面對自己的臨界線,聽見埋藏底心的聲音。…….她向前幾步又後退,抓著心窩深呼吸,有那麼一刻,我走進她深切的恐懼和憂慮,瞬間重疊上自己的,不知為何眼眶竟紅了。」
三、向外走也是向內走
「向外探索的同時,也會不經意向內走,走入內裡深深的叢林,那裡纏繞著對舒適文明推崇的藤蔓、對理性大腦和社會主流價值深刻信奉的荊棘,禁不起任何砍殺—-親愛的我們不需要砍殺,但我們可以練習疏伐」
曾經上過為期兩個月的登山課,
我常常很傻的在想:「哪樣比較不容易?」然後嘆一口氣,都很難啊。多少次動念中輟登山課,對體力差廢宅如我實在好艱辛,但怎麼說呢,就是不甘心,不甘心辜負自己,還有的一點渴望:渴望看見新的可能性,渴望能變強carry隊友而不總是被照顧的那個……
「迷失在起伏不定的各種生命地形裡,多數人寧可選擇自已限制在一條路上,也不願面對毫無標示的荒野那種令人無所適從的自由。」
手握指北針,緊捏著地圖和導航計畫書,和隊友互相照顧和扶持,或許,我們終將在荒野中,趨近那珍貴無比的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