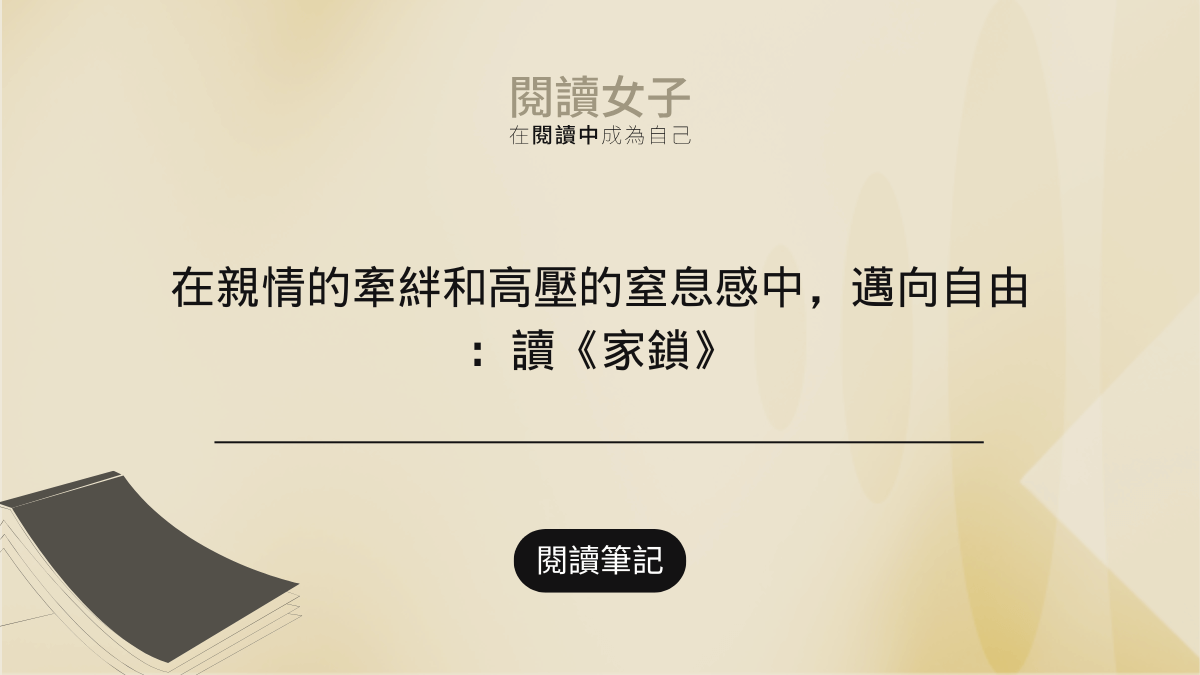「我檢視和家人的互動紀錄,通訊中浮現的情感細碎混雜,那個親情的牽絆是真實的,但那個高壓的窒息感也是無比真實。家庭這隻巨獸,對居於裡面的成員,往往同時滋養又同時傷害」
《家鎖》的作者是香港資深記者 譚蕙芸,長年關注弱勢屢獲獎項肯定,卻囿於原生家庭:哥哥有情緒病,父母皆高齡也生病,爸爸長年否認一切,媽媽跟著配合,也要求小女兒封口。無奈高齡父母再也無法照顧自己和生病的中年兒子,她「一打三」,費盡洪荒之力把家人從加拿大帶回香港照顧。
期間還得面對險惡的疫情、家人的不諒解、親戚的質疑、自己身體也出現狀況。厚厚的一本書,讀來步步驚心,擔心作者在哪裡就撐不住。幸好有許多朋友支持、長年累積的社會資本,作者也勇於向外求助,有意識地點點滴滴為這個返港家庭織就一張安全網。
「我們的家庭氣氛,從來不鼓勵坦誠溝通。整個家庭,對自身所處現狀,常處於逃避和否認狀態,未能有自我反省帶來的澄明時刻」
「家裡的氣氛就是偽裝、壓抑、窒息」
「這輛車子,就是我們家的隱喻。家裡只有一個人掌握大權,其餘的人要不主動就是被動配合,即使父親決定有什麼偏差,也沒有人有異議,車子就這樣向危險的路線直駛下去」
「在我父的世界裡,他不可以向別人承認自己犯錯,犯錯的當然是其他人,例如是可以犧牲的小女兒」
讀這本書,彷彿看見自己和許多朋友描敘過,原生家庭的狀況。華人家庭不鼓勵坦誠溝通,父母和子女未必能以真心相待,而是以在家中的角色去看待:身為兒子就是要光宗耀祖、身為小女兒就是沒什麼說話的權利。
幸好相較於哥哥,作者從小就懂得反抗,求學和工作經歷,更為她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門,不再困於原生家庭。當她回頭去追尋,哥哥當年到底怎麼了?有一個段落很打動我,她訪問到一位曾教過哥哥的老師:
「三十年後,這位曾經於中學時代叫過我哥生物兩年的老師,以和藹憐惜的語氣,解構我哥在中學時的歲月,教育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,大人們可以做多一點點什麼。我內心充滿感激。他是唯一一個成年人,承認做得不夠的,這對我來說,已經足夠。」
希望我也能成為,那個勇於承認自己做得不足的老師。
「我開始明白,物以類聚,人以群分,父親的朋友和他價值觀相似,愛用金錢和物質衡量事物,他們均認為,前輩教訓後輩是理所當然,後輩要虛心接受……當我向父親轉述叔叔的話,我父不但沒有替我說話,反勸說我要忍氣吞聲。我漸漸明白,原來當我遇到不公平待遇,父親不一定替我出頭。我還同時學習到一個道理,將來照顧路上,我要找更多志同道合、擁有跟我類似價值觀的人來幫忙。」
作者和家人多次「交手」,漸漸明白:得要尋求外援,家人不一定會挺你。放下期待後,才能務實地處理事情。這點令人敬佩,多少人直到年長,都還放不下對父母的期待?
佛洛姆在《聆聽的藝術》中這麼寫:「一個人的成長以變得自由為開端。自由的過程由一個人和父母的關係肇始。如果一個人不能從父母手中解放自己,如果他沒有越來越感覺自己有權為自己做決定,如果他不覺得自己對父母的願望既沒有害怕也沒有特別藐視,那麼通往獨立之路的門就總會是關的。我會說一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問自己:從我對待父母的態度來判斷,我在通往獨立的道路上走到哪裡了?」
漸漸長出力氣的作者,開始學會和父母打交道:
「妳母親不喜歡請外傭,我們不需要外傭」事實是,他自己不喜歡,但習慣說成妻子的意願。
我回他一句:「不聘請外傭,我這個女兒也沒法照顧你了」
而在向外連結照護資源的過程中,作者也發現:
「原來讓我多講一次,並不是經歷多一次創傷,而是經驗多一次療癒。不同的專業人士,如同多面鏡子,回饋了不同觀點給我。我的視覺愈來愈開闊。我漸漸覺得,自己不只是處理小家庭的問題,我像抽離了一些,可以用他者的角度回看自身。」
這本書讓我想起好多可以點滴串起的書:同為盡責的女兒,要面對家庭議題的《長女病》;同為女性,必須長照「一打四」的《錢先花光還是命先沒了》;討論對人生影響深遠的手足關係的《兄弟姊妹心理學》;為求保命,和原生家庭保持距離的《拋棄母親》…….
韓國小說《女大當家》帶有作者李瑟娥的自傳色彩:和本書女主角同名同姓的作家李瑟娥,1992年出生於首爾。2013年出道成為寫連載文章的勞工,某天決定開始寫無人委託的連載文章,大受歡迎,藉此償還了2500萬韓元的學貸。《女大當家》是她的第十一本作品。
書中女主角瑟娥,出生在商人之家,深得白手起家的爺爺疼愛,決定自己長大後也要:當老闆。長大後的瑟娥,在自己買的房子開了一人出版社,雇用母父,一起打造幸福人生。
希望有一天,身為女性、身為女兒不必再總是被預期為長照預備軍,「最好的長照保險」,而是能理直氣壯,成為掌握人生自主權的女家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