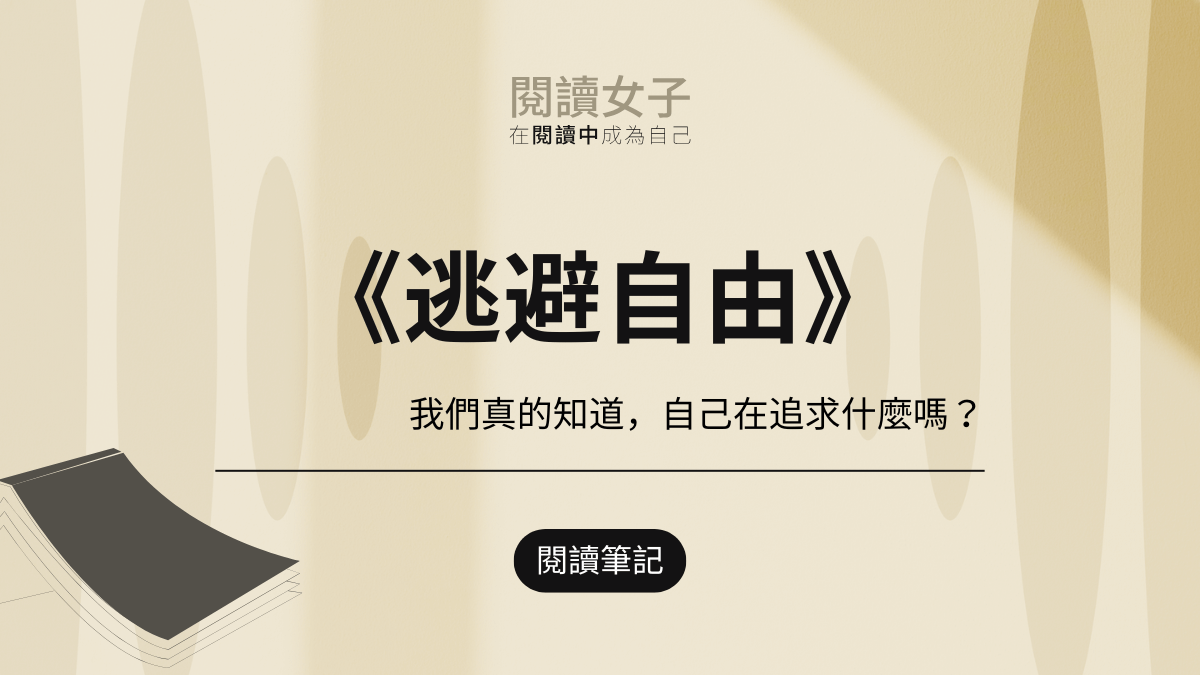本書出版於1941年,距離佛洛姆最為人熟知的《愛的藝術》出版(1956年),相隔了十五年。佛洛姆在書中說明,在自發性實現自我的過程中,個人能重新與世界、與他人、大自然、以及與自己產生連結,才是真正的自由。這樣的論述,也和之後的「創造性人格」遙相呼應。
一、閱讀本書前的三個問題
1.到底什麼是「自由」?現代人如何理解/誤解所謂「自由」?
2.人為什麼會想逃避自由?
3.新教教義和資本主義,如何塑造當代人的社會人格?
二、自由是心理學的問題?
1.佛洛姆說明本書用意:「經濟與社會問題確實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形成。但此外,還必須理解人性的問題。本書在分析現代人的性格結構中,使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甘願放棄自由,同時普遍存在於我們民族千萬人之中的那些強有力的因素。」也就是「心理因素」在社會演進與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。
2.本書預設:心理學的關鍵課題乃個人與世界之間獨特的連結,而非個人的本能需求未獲得滿足或遭受阻礙;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並非靜態,社會不只有壓抑性的功能,同時也具有創造性的功能。歷史造就人類,人類也造就歷史。
3.「適應」:「靜態適應」是個人在整體性格結構未變動的情況下去適應某些模式,也就是採用某種新習慣,例如從刀叉改成用筷子;「動態適應」是會引發新的驅力或形成新的性格特質。
4.人類本性並非是生物學上固定和與生俱來驅力的總和,也不是既定文化模式下毫無生氣的追隨者;人的本性應是人類演進的產物,具有獨特的運作機制與法則。
三、個體化發展與意義分歧的自由
1.「個體化」:個人從與整體世界的初始連結中逐漸浮現的過程(初始連結發生在個體化過程前,提供個人安全感的依據,例如幼兒與母親的連結、中世紀時期人們與天主教及所屬階級之間的連結等等)
2.一旦「個體化過程」完成,個人便脫離這些初始連結,不過這時他也面臨新的挑戰:要在所處的世界中尋找新的方向與根基,並以新的方式中找安全感,於是此時的自由就與前個體化的自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。
3.個體化發展的兩個面向:幼童在心理、生理等方面日益成熟,也越能整合成「自我」;同時感到孤立無援,被迫面對外在世界的各種冒險。
4.人如何面對焦慮和孤獨:第一、放棄「個體性」,但必然導致某種屈從,也會產生敵意與反抗意識;第二、與他人及大自然建立自發性的關係,也就是愛與生產性工作。
5.人類這個物種的發展史,也可視為逐漸個體化與自由發展的歷程。
人類的存在感建立於當來自生物本能的行為減少到一定程度之後,也就是當人類對大自然的適應方式不再具有強制性,或當人類行為模式不再受限於遺傳性的既定機制。「存在感」和「自由」,從一開始就密不可分。這裡的「自由」是指「消極意義」上的「擁有自由以免受某事物侵擾」。也就是個人行為免於受到先天本能的全面制約。
6.「自由」對人類來說是一份意義分歧的禮物:人類在存在之初就面臨各種行為的抉擇,藉由創造的行為,從單純的被動適應環境轉為主動克服困境。
7.中世紀以降到當代社會的這段時期,西方社會的經濟環境歷經激烈變革,伴隨著人類性格結構的大幅轉變。要理解當代社會所謂的「自由」,必須從宗教改革時期著手,因為人類在這時奠定現代文明的基礎。
四、宗教改革時期的個人自由
1.中世紀社會與文藝復興
中世紀早期:缺乏個人自由,卻不至於感到孤單與孤立。每個人打出生便在社會中擁有明確具體的穩固位置,並扎根於整體社會結構。個人與外界依舊保持初始連結,個人並未將自己或他人視為獨立個體。
中世紀晚期:「個人主義」在當時社會各階層萌芽,對有錢人和中產階級,產生不同的意義,也引發後續不同的回應。
這個時期的社會,個人不再受到經濟與政治的束縛,在新體系中有機會扮演積極與獨立的角色,同時脫離曾帶給他安全與從屬感的各種連結。新自由讓人產生不安、無力、懷疑與焦慮。
2.宗教改革時期
路德教派:人與上帝的關係奠基於因人的無力感而衍生的順服;接受自己的不重要,極力自謙自卑,並譴責個體權力,就能為上帝所接受。
喀爾文教派:宗教是根基於個人的無力感,人不應自覺是自己的主人,才能全心仰仗上帝的力量,「得救預定論」更加深人的無力感。(命運在出生前就被決定,平等原則被否定)
中產階級的焦慮與無力:為了逃避這種難以承受的不確定感,喀爾文主義的的顯著特徵是進行熱烈的活動,並努力做事,動機是對焦慮感的逃避。(容易演化成現代熟知的恐慌症或精神官能症)
將勞動與工作本身當作目標的態度,可被視為中世紀末以來,人類所發生最重要的心理變革。(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的自由人,會像這樣完全將精力投注在單一目標)
中產階級的敵意與憤怒:投射到上帝身上(設想其為專制又無情的存在);用道德義憤的方式間接表達;將敵意轉而針對自己(過度強調自己的邪惡與微不足道,或是將敵意偽裝成良心或義務)
總結:新教教義回應了那些恐懼、無根、孤立、被迫改變以適應新世界等人性的需求。經濟與社會的變革引發了新的個性結構,宗教教義則加強了這些個性結構,而這樣的個性結構也會回過頭來,成為形塑未來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因素,例如:工作的驅迫力、極度節儉、禁慾、強迫性的責任感、將生命視為滿足權力目的的工具等等。
五、現代自由的兩種面向
資本主義對「個人自由」的發展所造成的矛盾現象:使人更獨立、自主、具批判能力;感到孤立、孤單、恐懼。
資本主義中的普遍特徵:個人主義的活動原則(在增進「免於受到外在約束的自由」的同時,也間接切斷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連結)
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將人變成一種工具,服膺於人自身之外的經濟目的,並增強了新教主義已為人打好心理基礎的禁慾主義。
人們無法繼續承受「免於受到某事物侵擾之自由」所帶來的負擔,除非他們能從消極自由進步到積極自由,否則他們便必須試著逃避所有的自由。在我們時代的主要逃避方式,第一是像法西斯主義國家對領袖的完全順從,第二是個人對外在規則強迫性的遵從。
六、逃避機制
#「正常」和「健康」:可以從社會功能和個人觀點兩種方式來定義,但「讓社會順利運轉」與「個人圓滿發展」的目標並非一致。
1.權威性格
個人放棄自我,將自我與外在某事或某物焊接在一起,以獲取自我所欠缺的力量,也就是尋求「次等連結」來替代已喪失的初等連結。
常見:受虐和施虐這兩種行為,其實來自相同原因(無法忍受自己的孤獨和軟弱)而產生的「共生」;權力慾是施虐傾向中最重要的表現形式。
「施虐-受虐」性格的獨特之處,多半表現在他們面對權威時的態度。這類人崇拜權威,有向權威順服的傾向,同時自己也想成為某種權威。 這樣的人不相信平等,同時認為人生由人類自我、利益與願望之外的其他力量所決定,需要完全歸順這些力量。
2.毀滅性格
意圖摧毀對象本身,雖然自己仍是獨立與孤獨的,但所擁有的將是值得驕傲的孤立感,因為不在被外在具有壓倒性力量的對象所擊倒。 人們身上毀滅性傾向的程度,會與他在發展人生時所遭受到的限制程度成正比;毀滅性是無法實踐自我生命的後果。
3.機械化的順從
完全採取文化模式給他的人格類型,「自我」與外界的差異消失了。
七、自由與民主
「積極自由」:意指對個人獨特性的充分肯定。人生而平等,但也有與生俱來的差異性,自我若要獲得真正的成長,必然奠基在這種獨特性上,個人自發性地展現出完整且健全的人格。「自發性」的前提之一在於接受個人的完整人格,不再將個人切割成理性與感性兩種層面。唯有當人完全了解自我,人生經驗的所有層面達到整合,個人才有可能實現自發性的行為。
我們可將「藝術家」定義為「能自發性地表現自己的人」。
Q.為什麼自發性行為會引領人們獲得真正的自由?
在自發性實現自我的過程中,個人能重新與世界、與他人、大自然、以及與自己產生連結。個人在自發性行為中擁抱著外在世界,他的自我不僅完好無缺,甚至變得更強大穩固,因為自我的堅強程度會與其積極主動的程度成正比。
個人如果能克服對自身與生命處境的基本疑惑,以自發性的生命活動去擁抱全世界,與世界建立關係,最終就能以個人的身份獲得力量,並得到安全感。新的安全感是動態的,不以保護為基礎,而以個人自發性為基礎,唯有自己能給予。
八、總結與其他
本書從「自由是心理學嗎?」起筆,先討論個體化發展與自由的關係,接著回頭爬梳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對形塑社會人格的影響。而太過看重自由的光明面,而忽略其陰暗面的後果,就是讓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趁勢興起。人失去初始連結後,要面對焦慮和無助感,發展「積極自由」是不可或缺的,而民主、社會、經濟體制等等如何和個體化發展交織,也是作者關心的重點。
一開始的三個問題:
1.到底什麼是「自由」?現代人如何理解/誤解所謂「自由」? 佛洛姆將自由分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。人為了逃避孤獨感和焦慮,會選擇種種逃避手段,但會導致某種屈從和壓抑的敵意。唯有自發性行為(積極自由)能讓人與世界連結,不會消除個人主體性,也能獲得安全感。
2.人為什麼會想逃避自由? 初始連結消失後,人必須得面對焦慮和孤獨無依感,有人會選擇與他人「共生」、依附外在權威等方式來處理自己的情緒。
3.新教教義和資本主義,如何塑造當代人的社會人格? 經濟與社會的變革引發了新的個性結構,宗教教義則加強了這些個性結構,而這樣的個性結構也會回過頭來,成為形塑未來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因素,例如工作的驅迫力、極度節儉、禁慾、強迫性的責任感、將生命視為滿足權力目的的工具等等。
讀完此書後留下的疑問:
1.p.239,作者要如何定義「低階中產階級」?
2.p.144寫道:「現代人如果想出售商品或服務,便需要具備某種特殊的人格—-這種人格應該是討人喜歡的……就像任何一種商品,是市場決定了這些人格特質的價值,甚至決定了這些人的存在價值。」這段話讓我想到,現在流行的「人設」。為了求流量求變現的「人設」,是否會如佛洛姆所說,造成人與自己的關系的工具化與疏離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