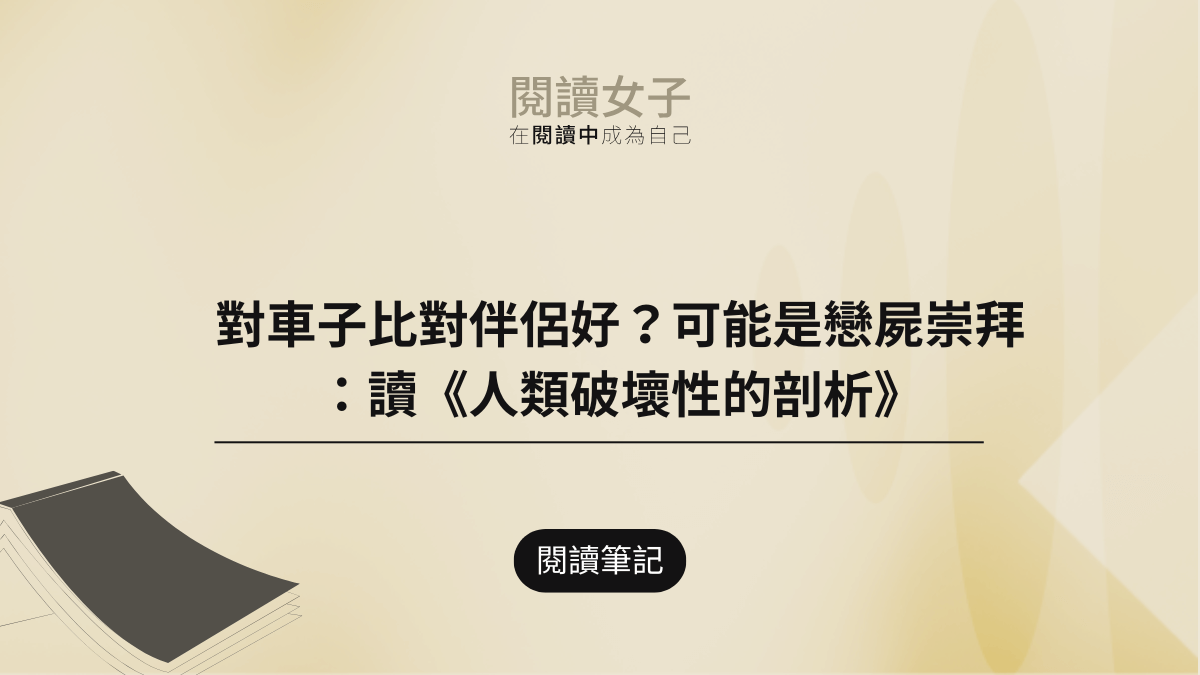日前有則報導:陳姓女網友在「女人的美麗與哀愁」臉書社團,問其他女性臉友「老婆把車開出去ㄎㄟ到,老公會罵嗎?」,有近500則留言回應,有人妻回應「會離婚」,或是「被罵得狗血淋頭」,也有強勢人妻回應「老公翻白眼就被我惱羞成怒地罵了一頓」。
有些人把車子看得比伴侶重要,佛洛姆在半世紀前就發現了!
廷貝亨:「人是唯一的集體屠殺者,是唯一不能適應自己社會的生物」
1973年,佛洛姆出版《人類破壞性的解析》,距離他出版自己最負盛名《愛的藝術》已有十七年。(《愛的藝術》在1956年出版)
《愛的藝術》提出重要洞見:人要如何學習和實踐作為一門藝術的「愛」。但兩次世界大戰後,接連而來始終未平息的國際紛擾,讓佛洛姆思考:人類(過度的)破壞性從何而來?
人類生而具有戰爭傾向之說,不但與歷史紀錄不合,也與原始戰爭的歷史不合。我們已經指出,原始人(特別是狩獵採集者)是最不好戰的,而他們的戰鬥也比較沒有破壞性和嗜血的傾向。我們也曾說過,戰爭隨著文明的進步越來越多,嗜血的傾向也越來越強。
佛洛姆爬梳人類歷史、古生物學、人類學等等,將人的攻擊性分為兩種。
前者是防衛性、反應性、屬於良性攻擊性,是人的生存所必須的;後者是人類特有的毀滅性傾向和絕對控制欲,屬於惡性破壞性,也是此書討論的重點。惡性攻擊性是人所特有,不是從動物本能衍生出來的。
科技與戀屍崇拜
惡性攻擊性既然不是從本能而來,那是怎麼出現的?
佛洛姆區分「本能」和「性格」。前者屬於自然範疇,後者屬於文化性、社會性的範疇,也就是為了適應社會環境所產生的。
性格是由一切非本能的欲求所組成的,相對持久的體系,人經由它讓自己與人的世界和自然界發生關連。當社會環境使人無法愛人也無法好好被愛時,就會出現惡性破壞性。
四百年前的科學革命開始,帶來新時代思維,有了量化和系統化:兩個世紀前的工業革命,這種新時代思維掌控的對象,從自然轉移到人類,現代社會是一個為計算而計算的世界。當生而為人的需求因大環境沒有被滿足,人的破壞性是現代體制下的惡果。
惡性攻擊性中的一種稱之為「戀屍癖」,是一種對死的、無生命力的東西強烈迷戀的性格特徵;其心思完全被純粹機械性的東西佔去。
佛洛姆這麼形容過度愛車者:
整個工業化世界到處都有這樣的人,他們對汽車比對妻子更有情感,更有興趣。他們為愛車而驕傲,珍而重之,親自清洗(儘管很多人不是沒有錢請人代勞),為它取暱稱。他們對車體貼入微,有一點點小毛病都大驚失色。
佛洛姆也強調,並不是擁有汽車就是戀屍癖,而是這些情形取代了對生命的興趣,取代天生的豐富生命機能,就是戀屍傾向了。
洞察破壞性從何而來,以愛安身立命
「破壞性是未被生活過的生活的結果」
佛洛姆認為,唯有創造適合人類成長的環境條件,讓人得以滿足愛人與被愛的需求,才能打破惡性破壞性的滋長。從日常生活的小事開始,先去注意我們在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失去信心,看穿我們用來合理化這種失去信心的情形的藉口。
看完此書後,我開始留意:當自己過度沉迷於某些無生命物(例如追劇、囤積食物….)是否也有些缺乏與自己、與他人、與世界愛的連結?